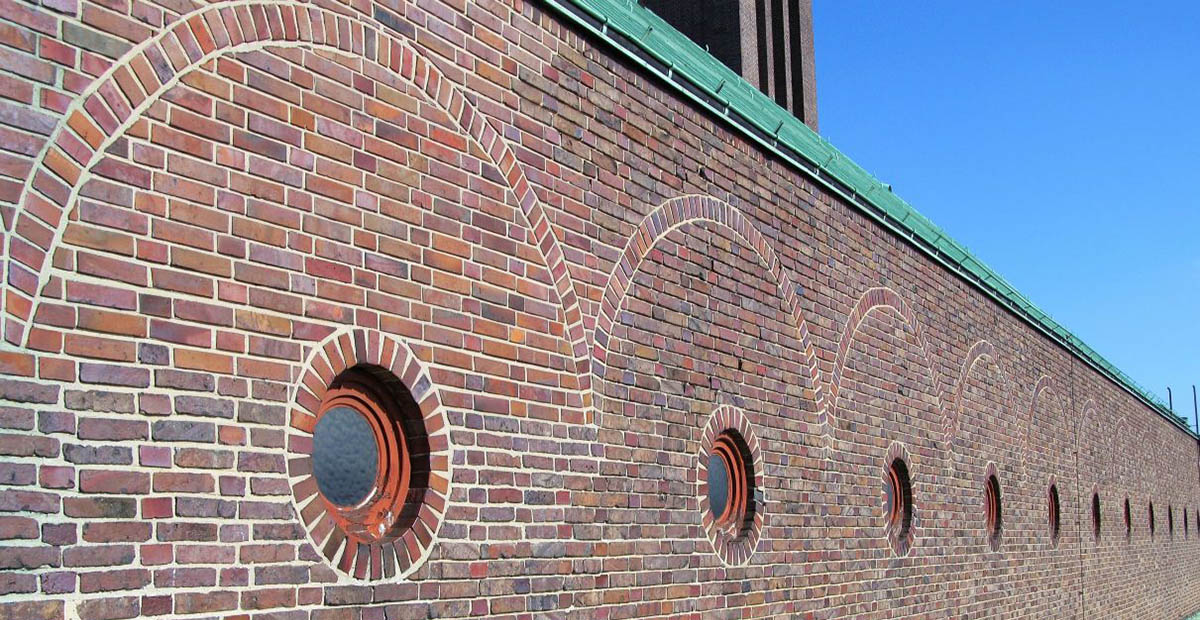没想到毕业后,一个的偶然的机会让我在柏林寻得一份博士后的工作,于是我和太太就在德国度过三年无忧无虑的日子。我每天早上骑十五分钟的自行車去上班,工作时基上都是对着电脑的,不需要对人有什么沟通,每天都对着DNA 的数据库分析,作图,晚上再骑十五分钟自行車回到家。通常回到家时,太太已经煮好晚餐,然后我可以放下一天的劳碌,与太太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晚饭时间。
饭后,我们会看看书或是念念德文,在德国中文书不多,但一对德国老牧师夫妇特别为华人建立了一个中文图书馆,让我们可以邮寄方式读到中文及信仰的书籍。我们家有台旧电视,是一位姊妹离开德国时留给我们的,不过我们没有看电视的习惯,所以也难得打开电视。星期天是教会聚会的日子,教会离我们家不远,我们常常骑半个小时的自行車到教会去,途中会经过跳蚤市场,动物园,西柏林的市中心区,度过这一段的时光是我们赏心乐事,有谁可以像我们如此这般地享受欧洲风情?教会里有一群很可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幼儿班的那群小朋友令我终身难忘。从德国出国旅行也是很经济实惠的,一年26天的假期总是显得特别多,我们闲时可以到处旅游,东欧西欧游了个遍。我们如两只懒羊,在青草地溪水边享受天父所赐予的一切。然而,安逸的生活却会让人渐渐失去继续作梦的勇气。
我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每天吃过午饭后总是随手拿起案头上的圣经或是一些从中文图书馆借來的书借,在校园里找一个角落,静静地消磨掉半个小时的时光。这个角落是校园里一棵很大的树下,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一棵什么树,但树上春露秋葉,夏荫冬雪都与我度过生命中的点点滴滴,这已成为我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是天气如何,我总会如一个忠实的票友等待大戏开场般静静地坐在它的荫下,翻一兩段的圣经,静静聆听一下上帝的声音,以及心灵里的回响。总在这样的时刻,我的梦就开始对我嗫嗫细语,他对我说:“你是否终其一生就是在学术界打拼,一级一级地往上爬,讲师,高级讲师,副教授,教授,总有一天你成了教授,受众人的敬仰,或者是在学术界独树一帜,成为一代宗师,开创学术界上历史性的先河?这些都是带着光环的荣耀,得到被人的赞美和羡慕,或者过上的优越生活上,大房子大車子,然后又如何?你的生命只有一次,你是否就愿意如此度过?”
那阵子,有一段经文常常在我心里回响,那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有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我总是每天都想到这段经文,特别那句”君尊的祭司"在我的脑海里好像总是挥之不去的。上帝,您是否有话要讲?从中文图书馆借來的杨牧谷的《还我祭司的丰荣》给了我一个清晰的答案。当然,作祭司就是成为上帝和人之间的桥梁,把人切身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也把上帝的爱带入人群。每个祭司都有一个祭坛,这就是我的职业,在它以上把自己的才能如破瓶的香膏一次过毫无保留地献上,用馨香的祭去宣扬上帝悦纳人的禧年。但,回到现实中,我该如何是好?我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我所作的专业只是把已有的象牙塔变得更剔透玲珑,它给了我生活和荣誉的保障,却令我远离我所关心的人群。进世卫,那个曾经缥缈的梦又浮现在我眼前。上帝啊,您说我转行作公共卫生可以吗?回想起多年來,我从数学系换进分子生物学,后來又做起了生物信息学,每一次上帝都为我开了一条从未想过的路,公共卫生是最接近我所学所长的,也是最能直接接近人群的一门。我静默了,渴望在寂静中找到上帝一些蛛丝马迹,而上帝却一如往常保持着箴默,如隐藏了一般。上帝的呼召可以是如此地平凡,没有痛哭流涕的激动,也没有山崩地裂的震撼。临到我的却是一份由内而外的笃定和平静。我对上帝說:“这是你给我的梦,只要饿不死,我愿意去。”
如果有人能够为梦想贴上标价的话,我想代价一定不菲。否则,为什么这个世上没有几个人肯付代价去追寻自己的梦呢?清楚上帝的呼召是一回事,前面的路怎么走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想得到进入世卫的入场卷,公共卫生硕士是基本条件。我与同事說起这个想法,同事回敬了我一句:你都念到博士后了,还去操什么勞什子的心去再念一个硕士,不是自讨苦吃吗?事实上还不幸让我的这位同事言中。首当其冲的我们的腰包,入读公共卫生,无疑就是主动放弃了我在德国的奖学金。断了经济來源还不是最重要的,要命的是没有了奖学金,与之相应的工作签证就无法延续。当我收到洪堡基金会的合约中止信时,我们在德国的签证只剩下一个月的有效期。就是说,一个月内不能签到另外一份工作合约的话,我们就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上帝啊,难道我真要”壮志未酬身先死”吗?这个梦也作得太短了吧?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眼看离签证限期只有兩个星期了。就在这紧要关头,没想到一直喊穷的老板居然勒紧了腰带,自己掏腰包继续雇用我半年时间,只是把全职的工作改为半职。这无疑对我们还是一个信心的考验,薪水只剩下原來的一半,还要交学费,加上來回柏林和汉堡大学(公共卫生硕士的课程在汉堡)之间的車费,及兩个人的生活费,可谓是捉襟见肘了。不过所幸的是,移民官大笔一挥,大方地给了我们七个月的签证。此时,汉堡的公共卫生课程已开学了兩个月。我数数手指,加上剩下的一个月的有效期,刚好可以完成第二学期的学业,还满有恩典地留下三天时间让我们收拾行装。第三学期是让学生写論文,不用上课,也无须留在德国,可以在海外完成。上帝是位精明的上帝,他說成,就成了。
零八年五月六号,结束了在以色列了兩个月的公干,我们乘坐晚班飞机回到柏林时已经是破晓时分。來不及回家休息,我睁着惺忪的眼睛,坐上开往汉堡的特快列車,开始了我的学业。因为我已经耽误了兩个多月的课,我一边自己把课补回來,一边要念新的功课,同时还要继续在完成柏林的博士后的半职研究工作。在汉堡的那段日子里,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我睁开眼睛就开始念书,闭上眼睛就睡觉,只觉得太阳还没有升上去月亮就已经出來了。只身在汉堡,太太不在身边,吃得就十分随便。从超市买來了蔬菜和肉,全都放在电饭锅里与饭一起煮熟。有时候,忘了买盐和酱油,吃下去的一点味道都没有,反正食物是为了肚腹,然而上帝叫兩样都变朽坏。课程是密集的课程,就是說理论课都在三个星期内教完,然后接着下來的三个星期是给学生做功课的,学生不必到学校來。因此,我每三个星期就可以回柏林继续我的研究工作,同时记着不要把功课拉下。如此一來,虽然工作和学业两不误,但日子难免过得有些极端。每个星期除了上教会和小组的那段时间,其余的时间,就是一天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是在电脑前度过。至于旅游,那也甭想了,一來没钱,二來没时间。
我一直以为,进世卫就是通向我的梦想的康庄大道。上帝却借着一件事來告诉我的使命。我开学不到一周,中国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5.12四川大地震。那些令人寸断肝肠的场面是始终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可以为我的同胞们做些什么呢?灾后的重建不只是食物,水和住房这么简单,这些只是肉体上的需要。对灾民而言,更加长远深层的影响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以及因失去亲人而造成的心灵创伤。更远一点的还有社会的公义,例如,如何为那些葬身于豆腐渣工程的校舍里儿童的家庭讨回公道,及以后防止同样的工程重蹈覆辙。这些的问题无不抽搐着我的心。我想,如果我能用所学的重整中国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系统,把我们信仰里上帝的博爱和公平多一点融入到中国的国策里,我们的同胞可以少受一点苦,在苦难中可以多一点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能够因着基督徒身体力行的見证而体会到上帝的慈爱,在苦难中有仍然有盼望,那是多么好的事啊。
我很清楚我的梦在中国,总有一天我会回到这片的热土,为着中国那些无人挂念的弱势人群而努力。在此刻,我仍然为这个梦想努力着。汉堡的学业刚已结束,乌干达的三个月的经历让我们体会了真正的贫穷。从乌干达回到悉尼接受母校的教职,又为我打开了一扇服侍中国的艾滋病人群的窗。从悉尼到北京,又给予了我与中国卫生部高层接触的机会。我知道这是上帝的手在一步一步地牵引我们的脚步,梦虽然还是很遥远,我却甘心做一个寻梦者。